《范雎说秦王》评析
会面前,昭王已闻有“秦危累卵”之言,心个早已是悬旌不定,所以开始时便“庭迎范雎,敬执宾主之礼”、“屏左右”、“跪而请”,欲得一言而后快。面对殷殷跽请的昭王,范雄却仍保持清醒的头脑,深知此次游说的难处,“皆匡君臣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所以便欲言不言,只是“唯唯”。说客游说人主实非易事,弄不好会有生命之虞。范雎以一籍布衣的身份游说秦昭王,正如他所说“交疏言深”,这时,他对秦王的心理状况与性格特征还不十分清楚,秦王喜欢听什么,想要干什么,他还没有准确的把握。因此,他必须先加试探,察言观色。他要贡献于秦王的谋略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废逐把持朝政的以宣太后、穰侯为首的“四贵”。而秦王与他们有骨肉之亲,并且是在他们的拥立下才得以即位的。范雎明白,若稍有不慎,就会“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所言甚深而交情甚浅,范雎能不顾虑吗?所以他吞吞吐吐,疑虑重重,回环往复,拖拖沓沓,而同时却又引古论今,援他况己,旁敲侧击,铺张扬厉。一方面对秦王反复进行试探,看他是否真心信任自己,是否能听从建议摆脱骨肉之亲的羁绊而自强自力;另一方面又反复申述自己对秦昭王的无限忠诚。在“何患乎”“何忧乎”、“何耻乎”的层层叙述中,对秦昭王展示自己的忠心,甚至表示“臣死而秦治,贤于生也”,好像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
待昭王说出“先生不幸教寡人乎”一语,已见其恳,范雎方才开始进言。他先引周文王与吕尚一例,得出“交疏言深”一语,因“交流”而难以“言深”,是王三问而不答的原因。范雎道出这一语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他先以“死不足患、亡不足忧、为厉为狂不为耻”总起论说之纲,紧接着便以排山倒海之势,一路耸动和要挟,步步深入和逼进,论说开来。他列出五帝、三王、五霸、乌获、奔、育之例,表明自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又借伍子胥一例,表白自己为使游说能行“加之以幽囚,终身不复见”也无患,若能“补所贤之主”,“同行于箕子、接舆”也是“臣之大荣”!其肺脏之言,感动了昭王。范雎认为时机已到,才真心吐露自己此行之目的:“足下上畏太后、下惑奸臣、不离保傅,终身暗惑”以至“宗庙覆灭,身以孤危”才是吾所畏、吾所忧、吾所恐耳!“臣死而秦治,贤于生也”作结,可谓卒章显志,愈显其一片赤诚和忠心。范雎雄辩之才,展露无遗。全文婉转而下,一路紧逼,言辞恳切,真挚动人。正如刘扔所评述“烦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文心雕龙·论说》)
本文在艺术上的显著特点是语言的雄辩性,文辞优美,生动而警辟。委婉说理时,真切生动,如涓涓细流,表白忠心时,铿锵高亢,一气呵成,又势如破竹。就在这滔滔的论说中,成功地勾勒了一位处事严谨,卓尔不凡,具有雄奇胆略和高超的论辩艺术的高士范雎形象,给读者的印象深刻,是《战国策》人物画廊中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形象。
《齐宣王见颜斶》出自《战国策·齐策四》。文章写士人颜斶与齐宣王的对话,争论国君与士人谁尊谁卑的问题。颜斶公开声称“士贵耳,王者不贵”,并用历史事实加以证明。它充分反映了战国时期士阶层要求自身地位的提高与民主思想的抬头。颜斶拒绝齐宣王的引诱而返璞归真,既表现了士人不慕权势、洁身自爱的傲气与骨气,也留下了古代隐士明哲保身、逃避现实的缩影。
诗人佚名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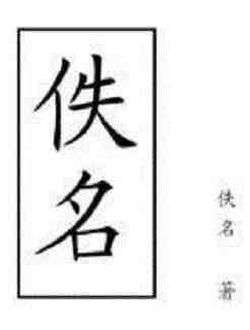
佚名不是没有姓名的人,而是作者没有署名,或是由于时间久远等原因作者的真实姓名查无根据,或者根本就无法知道作者是谁。也有的是由于集体创作或是劳动人民从很久远的时候就流传下来的作品,这样的作品..... 查看详情>>
诗人佚名作品: 《朱奴儿·你本是朱门少年》 《太平令·他可便约定把唐朝归顺》 《正宫端正好·腰间将百钱拖》 《十二月·父亲呵》 《邺民歌》 《脱布衫·喷香风扑鼻葡萄》 《东瓯令·畏奸雄言路绝》 《尾煞·你先将那血痕儿扫拂的乾》 《冬日书情·殊乡寂寞使人悲》 《逍遥乐·小旦上》
文言文《范雎说秦王》的名句翻译赏析
- 即使文王疏吕望而弗与深言,是周无天子之德,而文、武无与成其王也 - - - 佚名 - - -《范雎说秦王》
- 是日见范雎,见者无不变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跪而请曰 - - - 佚名 - - -《范雎说秦王》
- 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臣之事,处人骨肉之间 - - - 佚名 - - -《范雎说秦王》
- 故文王果收功于吕尚,卒擅天下而身立为帝王 - - - 佚名 - - -《范雎说秦王》
《范雎说秦王》相关文言文翻译赏析
- 古诗《水仙子·一江烟水照晴岚》- - 创作背景 - - 作者:张养浩 2021-02-18
- 古诗《七夕偶题》- - 注释译文 - - 作者:李商隐 2020-05-27
- 古诗《渡江·大江骇浪限东南》- - 注释译文 - - 作者:雍正 2020-03-08
- 古诗《别梁锽》- - 鉴赏 - - 作者:李颀 2020-02-21
- 古诗《朱詹吞纸苦读》- - 注释译文 - - 作者:无名氏 2019-04-15
- 古诗《狮子王与豺》- - 注释译文 - - 作者:冯梦龙 2019-02-09
- 古诗《秋怀·节物岂不好》- - 创作背景 - - 作者:欧阳修 2019-01-15
- 古诗《萧何追韩信》- - 白话译文 - - 作者:无名氏 2018-09-07
- 古诗《阴兴传》- - 注释译文 - - 作者:范晔 2018-09-06
- 古诗《浣溪沙·闲弄筝弦懒系裙》- - 创作背景 - - 作者:晏几道 2018-03-20
- 古诗《清平乐·春风依旧》- - 创作背景 - - 作者:赵令畤 2018-01-13
- 古诗《寒夜·寒夜客来茶当酒》- - 赏析 - - 作者:杜耒 2017-12-24
- 古诗《鹧鸪天·休舞银貂小契丹》- - 赏析 - - 作者:范成大 2017-11-27
- 古诗《蝶恋花·雨霰疏疏经泼火》- - 注释译文 - - 作者:苏轼 2017-10-31
- 古诗《穷边词二首其一》- - 注释译文 - - 作者:姚合 2017-05-03
- 古诗《秋闺思·秋天一夜静无云》- - 创作背景 - - 作者:张仲素 2017-04-21
- 古诗《绝句四首其一》- - 注释译文 - - 作者:杜甫 2017-04-07
- 古诗《狡童》- - 注释译文 - - 作者:诗经 2017-04-04
- 古诗《东海有勇妇》- - 注释译文 - - 作者:李白 2017-03-15
- 古诗《郭隗·逢时独为贵》- - 鉴赏 - - 作者:陈子昂 2017-03-06